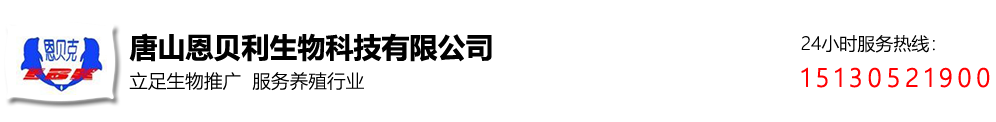| 国内增殖放流必须弥补科技缺乏之殇 |
| 5月中下旬,我国福建、广东、辽宁等沿海城市进入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季节,各地增殖放流的浪潮此起彼伏。作为增加渔业资源保有量的一种重要方法,随着这些年我国增殖放流投入和放流规模的不断膨胀,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明和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增加的问题日益突出。

大头鲤(大头鱼)是云南高原湖泊特有的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鱼类。在星云湖这个云南水产养殖业的天然场所,闻名全国的“江川大头鱼”目前已销声匿迹。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团队近年来一直从事云南珍稀土著鱼类的保育和增殖放流工作。课题组副研究员潘晓赋介绍,土著大头鲤与外来鲤的渐渗杂交已在星云湖野生种群中广泛发生,能够采集到的“大头鲤”形态介于大头鲤和普通鲤之间,不合理的增殖放流正是导致其灭绝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受到威胁的不只是大头鲤。
通过向天然水域投放苗种恢复渔业资源,无疑对重建生态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国内增殖放流的发展越来越畸形化,增殖放流的盲目性突出,“什么种类都往里面放,什么东西都敢放,各个水域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大鱼塘’”。
杂乱的“大鱼塘”
“有人戏言,不合理的增殖放流使得各个水域成了一个‘大鱼塘’。这种说法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水产养殖系主任刘其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的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是一种通过向天然水域投放鱼、虾、蟹、贝等各类渔业生物的苗种,达到恢复或增加渔业资源种群数量和资源量的方法。
由于过度捕捞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世界渔业资源普遍衰退, 优质鱼比例变少、低龄化严重、渔业资源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日益严重。19世纪后期,美国等国家即开始采取增殖放流的手段拯救渔业资源。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开始启动水生资源的增殖放流工作。截至目前,渤海、南海、东海、黄海四大海域已全部开展增殖放流工作,内陆水域中,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已开展增殖放流工作。可以说,放流水域已覆盖境内全部重要渔业水域。多年的实践表明,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是恢复水生生物资源的重要和有效手段。
“然而,与国外增殖放流的系统科学性相比,国内增殖放流依然只停留在行政管理的层面。”农业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说,在国外,增殖放流被视作恢复种群多样性和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而我国既有的增殖放流工作多是从渔业规模的扩大和渔民增收的角度考虑,仅关注放流的数量。
以日本为例,作为世界范围内较早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国家之一,日本全国的都道府县都成立了栽培渔业中心,从事放流鱼种的选择以及放流规模等相关方面的研究,放流工作被视为系统性非常强的科学研究。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没有的。”有专家向记者透露,国内缺乏对于放流种类和规模的研究,放流仅是行政管理层面的工作。
2006年国务院颁布《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指出各地要积极有序地开展渔业资源增殖工作,而重点针对已经衰退的渔业资源品种和生态荒漠化严重的水域。自2008年起财政部每年批准3亿~4亿元资金投入到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中。
据了解,目前国内对于增殖放流的资金均由中央转移支付到地方,然后由地方政府进行招标,选择放流单位。
“招投标的方式对于保证资金安全具有一定效果,但对于生物物种来说并不适用。”上述专家指出,招投标方式完全是从资金管理安全的角度考虑,“增殖放流是一类科学性很强的活动,鱼种的选择和放流的规模、时间都需要作严格的科学评估,不能说放就放。而国内,科学的因素丝毫没有得到体现。”
危起伟指出,放流前缺乏起码的评估和科学考量,放什么鱼,谁来放,以什么样的比例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忧患的“大摊子”
“增殖放流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有专家向记者坦露自己的隐忧。
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全年共投入增殖放流资金超过9.7亿元,同比增长15.6%,放流各类水产苗种和珍稀濒危物种307.7亿尾(只),增长3.95%。国家对增殖放流的投入和重视日益增大。
“国内增殖放流的发展越来越畸形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而其带来的已经不是风险,而是看得见的严重后果。
对此,刘其根指出,水域生态功能的退化,除了污染环境外,也与国内大规模不合理的增殖放流有一定关联。
以中华绒螯蟹的增殖放流为例,由于经济价值高,中华绒螯蟹养殖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支柱产业。而湖泊水草资源丰富、环境条件好,成为其养殖的首选场所。
然而,由于放养不合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泊,如太湖、鄱阳湖等的水草资源都被破坏殆尽,甚至连一些中西部尚未开放的湖泊也难逃此劫,湖泊“藻型化”问题加剧,整个水域的生态系统完全退化,丧失了渔业功能。
此外,畸形的增殖放流还会造成水域水生多样性的丧失。
1958年,四大家鱼人工繁殖的成功,使我国渔业摆脱了依靠天然捞鱼的被动局面。然而,盲目的增殖,导致许多人工繁殖的养殖品种和天然水域的种群混杂,前者的遗传多样性显然低于野生种群,而经过长期的人工繁殖,也会导致其种群退化,这些因素都会给自然繁殖群体造成负面影响 。
“即使同样是四大家鱼,也要考虑放流的水系。”刘其根说,国内的人工放流都是基层单位在做,在其眼中,鱼都一样,到处都在放。“不是一个水系就是外来种,会导致当地的土著鱼类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乃至土著种的灭绝,新疆和云南都有类似事件发生。”
“种种事实表明,人工增殖品种的集中增殖会对水域原有水生多样性造成严重影响。”危起伟说,“亲鱼的数量少,基因也少,人为增加一些基因在种群内所占比例,那些适应野外环境的基因数量就会越来越少。”
除此之外,人工增殖放流可能增加野外种群暴发鱼病的风险,这也让专家非常担心。
“苗种是采用塘养的方式,高密度的养殖,鱼种暴发鱼病的风险很大,因此放流的鱼种经常携有病原体,把疾病带到野外。”刘其根说,在国外,买来的鱼种放养前会有检疫环节,而国内该环节一般被忽略。
随着增殖放流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单位和个人开展的增殖放流活动也在不断增多,科学有效的增殖放流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这些个体的放流主要是从花鸟市场购买。”潘晓赋说,不加挑选的放流,职能部门很难监管。
严重缺位的后期评估
对于增殖放流来说,放流效果科学评估是增殖放流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而要想评价放流的效果,后期对放流鱼种的监测不可或缺。
据潘晓赋介绍,监测内容包括放流地生境质量评价、放流种群与野外种群的遗传关系与生态关系以及放流个体的扩散与存活情况等。
“放流计划是否合理等都需要科学评估效果的反馈。”危起伟说,监测可为今后改进增殖放流策略、实施适应性管理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标记则是进行监测的重要方法。对人工繁育的个体标记后放流,并在放流后持续重捕,可获得人工种群的个体生长状况、种群动态及分布等信息。
在欧美等国家,对放流对象进行体外体内标记、坚持对渔获个体进行检查等有着一套完备的体系,以保证掌控放流物种的动向。
近年来,增殖放流常用标记法标扩外部标志和内部标志,可以根据放流种类的不同需求进行标记。外部标志方法有挂牌法、荧光标记法、切鳍标志法、贴签标志法等,内部标志法则有金属线码标记法、遗传标记法等方法,像金属线码和荧光标记可以用来标志规格较小的鱼虾蟹,大黄鱼、黑鲷可以用标志枪快速标记。
“但是,每一种鱼都要进行长期的试验才能发现哪一种鱼适合哪一类标记。”危起伟说,目前,国内大部分的增殖放流都没有做标记,而没有做标记则意味着监测无法进行。
事实上,在我国,有关放流后的种群监测研究较少,主要还是局限于研究机构小规模的研究,大部分的放流鱼种没有后期的监测。
“中央转移支付里是有5%的资金计划用于后期的科学评估和跟踪监测。”危起伟说,但出于便于管理的考虑,这些钱并没有用到后期的效果评估上去,各地的增殖放流没有配套的科学评估项目,“有的地方即使想做,但是没有相应的技术力量支持”。
此外,危起伟坦言,干扰评估的外界因素太多,也是国内后期评估监测缺位的重要因素,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强大的捕捞强度。
前段时间,2000尾人工繁殖的大规格中华鲟被放流。这些中华鲟是2011年繁殖的子二代个体,超过2岁龄,整体长度超过70厘米。这些中华鲟部分置入了声呐标记,并在宜昌、宜都、沙市、城陵矶、武汉、九江、铜陵、南京、江阴9个断面布设了声呐接收器,
“然而,放下去没几天,超过一半的中华鲟便监测不到了。”10多年来,危起伟一直致力于中华鲟的人工增殖放流研究,谈起这件事情,他又心痛又恼火。
“捕捞强度实在太大,每过一个断面,可监测到的数量就少一些。”危起伟说。
潘晓赋也指出,在很多放流现场,他们才将鱼苗放流出去,当地渔民就背着电鱼机电鱼,诸如此类现象极为常见。
危起伟指出,国内的增殖放流很多时候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放流——渔民捕捉——产量不增加——再放流,“没有后期科学的评估,一个品种进行增殖放流有没有用,都说不清楚。”
必须要注意的是,监测评估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必须有持久性。而现在,农业部仅有的几个行业专项在做相关方面的试点项目,但是规模有限,而且时间非常短。
“可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试验都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危起伟说,“要想了解鱼放下去会对生物量以及遗传多样性产生哪些影响,需要相当长的周期和科学评估才能说明。”
以大马哈鱼和三文鱼的放流为例,其遗传衰退问题也是在放流了10多代后才被发现的。
中华鲟的增殖放流始于1997年,但危起伟坦言,直到今天,他也不能保障中华鲟放下去就能够有效。“中华鲟平均18年才会做第一次繁殖,现在还没到性成熟返回长江的时间,而且被放留的中华鲟,能否被回捕都很难说。”
放流效果的研究离不开对渔获物的研究。但是国内既有的监测渔获物的体系也受到了专家的诟病。
“整个监测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危起伟说,现有的监测都是靠渔民捕捞,且使用的网具和方法也不统一,监测不具有延续性,也不利于后期的评估。
将科学纳入放流计划
“当别的国家都已经在作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做的还是行政命令。”一位多年从事增殖放流的研究人员向记者感慨道,“国内的增殖放流计划缺乏科学的有力支撑。”
在刘其根看来,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是一项集水产养殖、渔业资源、渔业捕捞、环境保护、渔业管理等众多学科为一体的物种保护和资源增殖措施。在实施增殖放流过程当中,要保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涉及一系列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尤其是对于内陆水体而言,一定要考虑不同鱼种之间的关系,放流过程一定要考虑到多鱼种之间的平衡。而国内的增殖放流从总体规划到具体实施以及后期的监测,都缺乏科学评估的有效支撑,要使增殖放流能够起到实效,必须弥补科技缺乏之殇。
刘其根指出,我国实行的资源增殖放流资源养护政策和方案,出发点都是好的。但目前由于国内各水域鱼类资源缺乏有效的统计数据,使得放流效果的评价难度很大,难免使放流陷于盲目。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对增殖放流科学性的认识,加强对基础研究(包括鱼类资源的监测和统计)的持续支持力度,了解其更多的生活习性。
在我国,增殖放流工作主要由各级渔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企业承担放流工作,放流的门槛较低。而其后果则是科技研发能力严重缺乏,且存在以恢复水体生产力为目标的增殖和以恢复自然水体土著鱼类种群为目的的增殖的矛盾冲突。
“应该尽快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使增殖放流与科学评估双管齐下。”危起伟说,应该将科学评估纳入到总体设计上,而这包括放流前的鱼种选择、放流规模的确定以及对后期放流效果的监测等等,尤其是在后期的放流效果评估上,应该纳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应该由专业的队伍来做这个事情,避免放流流于形式。”
另外,针对国家将增殖放流视为资源增殖的中心任务,大规模生产、投放种苗及加大投入的趋势,专家呼吁应进行试验性增殖放流。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雷霁霖认为,增殖放流不能仅仅看经济效益,更重要的作用是改善渔业资源。
刘其根表示,有关研究实践表明,开展试验性放流,可为后期规模化增殖放流策略的制定提供基础依据,依托试验性增殖放流制定的放流策略,其实践效果明显好于缺乏该过程的增殖放流。
此外,恢复对鱼类资源的登记也成为专家关注的内容。
有专家指出,我国的渔政管理目前不是很有效,渔政部门仅关注渔民有没有捕捞证,而具体捕多少,使用什么样的网具,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说不在检查范围之内。
“必须要有专门的部门确定渔获量,不然基本的底子没摸清,增殖放流也很难做。”刘其根说。
另外,在资金的拨付上,危起伟也有着期许。
“放流的资金拨下来一般是在年底,时间严重滞后。”危起伟说,资金拨付与放流鱼种的生物学特征和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拿到资金开始放流,放流的鱼种在很短的时间内会被打捞掉。“希望资金的拨付能够根据各个水域的情况进行更合理的科学安排,能够支撑放流的过程。” | | | 来源:中国科学报综 时间:2014/5/30 15:54:46 |  |
|